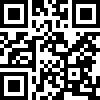作者:雅婷
编辑:王小笨
耿军是东北人,他拍的电影多和自己的家乡黑龙江鹤岗有关。
那里有低沉又灰蒙蒙的天空,废弃的火车轨道、失修的工厂设施和便宜的房价。对,5万元就能买一套房在2019年成为了鹤岗最显性的标签。采访耿军的第二天,他也在朋友圈转发了一条有关鹤岗房价的新闻,言语间颇有调侃的意味。
但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家乡仅仅因为房价低被人记得,他知道那里有某些更深刻的东西,他把它们称之为“后工业时代的荒废景观”。他就拍生活在这样景观里的人,用黑色幽默的腔调讲他们的悲喜交加,逐渐形成了一种独属于自己的风格。
耿军和一般印象里的东北中年人不大相同,他低调、内敛、讲话重条理、有幽默感但偏冷,在 HiShorts!厦门短片周见到他的几天,他都穿着一件蓝色长袖T恤,脚蹬着看不出品牌的运动鞋,即便是走红毯的时候也不例外。
说来也巧,几天前我的同事在三亚艺术季也见到了他,他们一起在 KTV 唱了歌,那几天他也始终穿着同一套衣服。这很耿军。

(耿军在 HiShorts!厦门短片周)?
耿军和名利场的关系并不密切,他醉心于自己的电影。2013 年他的短片《锤子镰刀都休息》在金马奖初露锋芒,2017 年他带着新片《轻松+愉快》重回金马,同时获得了最佳剧情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摄影和最佳原创歌曲四项提名。
2018 年底,耿军的新片《东北虎》在鹤岗开机,开机图里女主角马丽是红红的脸蛋还挺着个大肚,男主角章宇则是满脸胡茬,秋衣露出毛衣一截,电影的背景还是大家熟悉的“后工业时代的荒废景观”。
在厦门短片周耿军担任的是创投单元终审评委,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和他聊了聊还没上映的《东北虎》、房价很低的鹤岗和东北文艺复兴。
以下是他的自述:

《东北虎》最近刚刚剪辑完,现在在做声音、音乐和调色这样的后期工作。我们在鹤岗拍了大概两个月,回家拍踏实,因为自己对那个环境很熟悉也很喜欢,它能达到我们影像里的所有要求。其实在写剧本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规划剧本里的某个场景在哪儿拍,摄影和美术在重新选景是在我之前拍过的场景的基础上,因为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拍重复的场景。
《东北虎》的主角是章宇和马丽,和演员的沟通从一开始就特别顺畅,我也看过他们之前的作品,他们对我之前作品里的演员也是非常认可的,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做了一个融合。拍戏的时候我并不是让鹤岗当地的演员去向他们靠近,然后让我的演员演成他们的专业度。我们其实是反着走的,是让他们往鹤岗的环境靠,所以他们最后呈现出来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契合的表演方式,这种融合对于他们这样优秀的演员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大的难度。
在写剧本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要固定找谁来演,写完剧本后就有了一个 30 多岁,晚婚,刚怀上第一胎这样的女主角,所以马丽在年龄点上是适合的。很多人觉得马丽是一个喜剧演员,但她首先是一个演员,一个好的演员是可以驾驭各种风格和类型角色的,而且我觉得能演喜剧本来就是很难的。

(《东北虎》开机图)
其实我电影里的主人公和人物关系一直都在东北的景观里,只是故事的背景正好是2010年前后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,在那个时间段里就显得更现实。鹤岗就是我的家乡,(经济问题)这个事儿对我来说是现实存在的。我希望家乡现实存在的东西能被更多人看到,因为那里不单有便宜的房价,还有其他需要被别人看到的真实。
现在鹤岗只有当地或者黑龙江那种官方的报道,但这个真实感可能只有官方的报道是不够的,所以是需要一些其他报道来补充的,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承载一些呈现的义务。我不想让这些被遮蔽掉,这样一个地方太容易被遮蔽掉了。一个地方的现实就是如果自己要是不去关心那儿,其实它可能就被自己遮蔽掉了。
从2019年春天到现在,大家都在说房价的事情。我觉得鹤岗可能有另一个功能的出现,它能给这帮大城市里没有钱,还渴望买房的那帮人解压,你在这儿会觉得自己没有经济压力的问题。
前两天还有一个电影编剧问我,去哪儿租房可以安静写作,然后租房还没有压力。我说你去鹤岗,五千块可以住一年,而且鹤岗的纬度和北欧一样,下午三点半天就黑了,物价还便宜。也不用离开城市生活,物流都很方便,有一个特别大的综合购物中心叫时代广场,也有两家影院,这些都没问题。

我想用影像把那些即将消失的工业景观给留下来,但这样有什么意义,我也没想过。那些承载了三代人记忆的场景,那些大的工厂,煤矿或者是家属楼,是鹤岗的,也是我的成长经验。这样的新旧交替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,但在这个过程里,伴随着一些逝去的记忆,会有一些伤感的情绪,因为那些记忆都是有根据地的。
比如说我的小学还在,只不过现在已经荒废了,可能再过几年也就拆了。我每年回去的时候能看到记忆里一个特别具体的根据地,但是当这个根据地彻底消失之后,内心好像就没有那么踏实。因为人可能既需要继续生活,又需要以前的生活作为精神上的依托。
东北人的个性有共通的东西,有本地独特的东西,清醒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,“这里有那么多山珍!”我看街上走的那些人那么有趣和可爱的时候,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山里边的蘑菇,不是那种毒蘑菇,是那种特别可爱的山珍,但是当有一些特别糟糕的情况出现的时候,我就会觉得他们是山里的毒蘑菇。
那种情感其实特别复杂,我没有办法去美化东北人,我也没有义务去美化东北人,因为我特别特别自信,就是在这一点上我能特别清楚的知道,我所有的爱恨交织都源于我自己,源于我自己是个东北人。

(耿军出演自己的电影《轻松+愉快》剧照 )
我从没有用一种蹩脚的眼光去看待那个地区,或者是某一个人和那个群体。我对那儿的爱恨交织其实都是因为我在乎那儿。我对自己的不满也包含着我对那个地方的不满,我对那里的制度和人际关系等因素都是有切身体会的不满,我是其中的一员,我没法特别理智地对它,我也希望自己不要太理智,不要变成一个东北问题专家。我会变成一个提问题的人,一个不太客气地提问题的人。
我对其他地方可能会客气一点,但我对东北可能不太会客气,但我觉得我那种不太客气也是有温度的,我也希望那里给大城市的人带去的安慰能持久一点。我也听说因为有人写鹤岗房价的事,鹤岗现在的房价有点上涨了,要是涨一点还好,要是涨太多的话,我们也有罪恶感。

东北文艺复兴是一个新鲜的说法,但要靠一首歌来复兴吗?还是靠几本小说?我觉得那些作品都是特别好的,我都看过,但是还不够多。所谓复兴应该是,无论小说、音乐、电影还是电视,这些领域都涌现出了好的作品,才有可能呈现一个文艺复兴的局面,只靠一个口号是不够的。
我们看文艺作品,看完之后会去想说中国过得好的地方是哪儿?我们会参考一个样本,会觉得那儿过的好,为什么过得那么好,我们会研究它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爱看哪儿过的惨,我们要不要研究它?东北恰恰提供了一种有趣的表象,它可能在一个有趣的点上,大家就横向地来观看这些小说和电影。
但我觉得文艺作品本身能带来的东西是微乎其微的,大家是像看一个网红一样去看这个城市,或者说看东北。东北有三个省,我只说黑龙江省,其他地方不归我说,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用一个看网红的方法去看它,红半年就算了,大家就不太理它了。

(《轻松+愉快》剧照)?
我希望鹤岗这个城市,或者黑龙江地区不要被这样观看,我希望它能有更多的可能性,而不是被别人当成一种奇怪的事去研究它。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,像这种能源枯竭的城市多了去了,经济衰败的样本也多了去了,只不过是其中有一个受到了关注而已。
我们拍电影不是去研究一个地区,当一个地区的研究专家。研究一个地区不要根据《新闻联播》,也不要根据文艺作品,文艺作品有情感先行的东西。研究社会靠电影是不够的,靠小说也是不够的,但要是说提供一种情感,以及导演表现现实的温度,那可能是够的。
我也没有把在鹤岗创作当成一个前提摆在那儿。黑龙江有那么多可拍的,我未必非得在鹤岗耗着,中国有那么多可拍的,我未必在东北耗着,世界有那么多可拍的,我也未必在中国耗着。我觉得这些都是自由的,没有想过说一定非得在哪儿拍不可。
我这次在厦门短片周担任创投单元的终审评委,看片的时候发现的问题,也是整个创作环境里的共性问题。很多导演和编剧在某些理念上没有达成一个特别好的融洽度,就会拧巴一点。要不然就是想当然,要不然就是言不由衷的空,或者是一种坐在屋里面想象出来的真实生活,像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哪儿都有。
创作还是要从自己身边熟悉的东西入手,然后要有特别清晰的创作和制作思路,要是都能摸准就还好,但要是只想着创作不想着制作,写的时候挺飞的,到最后其实完成不了,在创作和制作之间找到平衡点,对大家其实都是难题,对我来说也一样。